1900年,在敦煌千佛洞里發(fā)現(xiàn)一本印刷精美的《金剛經(jīng)》,末尾題有“咸同九年四月十五日(公元868年)”等字樣,這是目前國內(nèi)發(fā)現(xiàn)的、最早的有明確日期記載的印刷品。
公元824年,元稹為白居易詩集作序,說道:“二十年間,禁省、觀寺、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,王公、妾婦、牛童、馬走之口無不道。至于繕寫模勒,街賣于市井,或持之以交酒茗者,處處皆是。”可見當時印刷術與手抄本曾并行。
印刷術在推動世界歷史發(fā)展中產(chǎn)生過巨大作用,被譽為“文明之母”。一方面,它大大降低了信息傳遞的成本,使普通人也可以獲得知識;另一方面,它形成了閱讀文化,使個體有機會與社會脫離,形成自我意識和個人思想。可以說,正是因為印刷術,人類重新反思既往的歷史與文化,對擺脫中世紀的文化禁錮有著非凡的意義。
有趣的是,印刷術在東西方歷史發(fā)展中產(chǎn)生的作用不盡相同。
在歐洲,印刷術推動文化傳播擴散的范圍和速度,使《圣經(jīng)》等書籍快速擴散,打破教會對知識的壟斷,對文藝復興的出現(xiàn)和發(fā)展有很大的作用。弗朗西斯·培根認為印刷術改變了“這個世界的外貌和狀況”,并提出的忠告:“要注意其威力、效應和后果”。興起于15世紀中葉的印刷技術革命對歐洲宗教改革、工業(yè)革命等帶來的深遠影響驗證了這句話的重要意義。
然而,作為發(fā)明印刷術的母國,它產(chǎn)生的作用卻并沒那么大。
據(jù)統(tǒng)計,1820年到1913年,中國每百萬人擁有圖書僅為3本,日本是7本,荷蘭是538本,瑞典是219本,英國是198本。當時西方學者曾說,東方給人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,那里很少能找到一本書。
書少,則識字率亦不高,清末中國人識字率僅16.6%至28%之間,而日本識字率在明治維新前已達40%。一方面,當時中國男女不平等情況嚴重,女性識字者很少,另一方面,雙方政府對社會的控制力度不同,導致清末私立學校的普及程度不如日本。不過,還有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中文字數(shù)太多,不方便印刷,影響了知識傳遞速度。
辦理中文印刷,至少要準備5萬左右活字,成本巨大,管理、檢索、排版起來也很難,所以雖然宋代中國已有活字印刷,但到明清時,雕版依然是最主要的印刷方式。
清代北京印刷較發(fā)達,書鋪林立,僅琉璃廠一帶就有一百多家,隆福寺街也是京都書肆繁集之處。有的以販賣為主,有的兼作雕版印刷發(fā)行。如老二酉堂、聚珍堂、善成堂、文成堂、文寶堂、榮祿堂、文錦堂、文貴堂、文友堂、翰文齋等,都是刻印兼發(fā)行的。但由于成本太高,所以老書多、新書少,完全圍繞市場運轉,從某種程度上,壓抑了革命性變化的產(chǎn)生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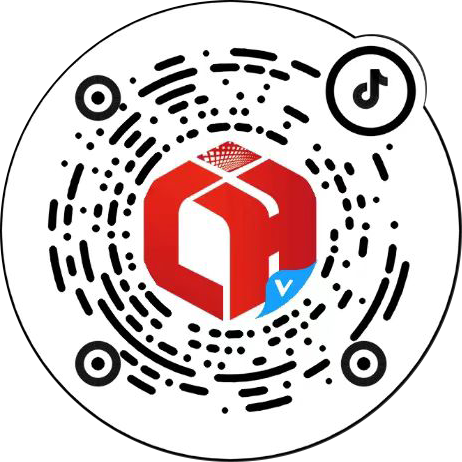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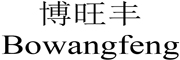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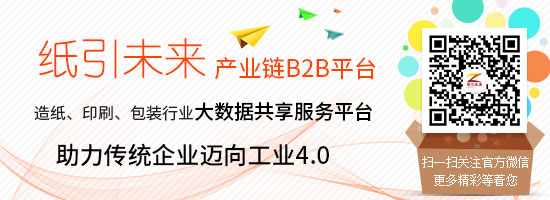





 行情
行情
 訂單
訂單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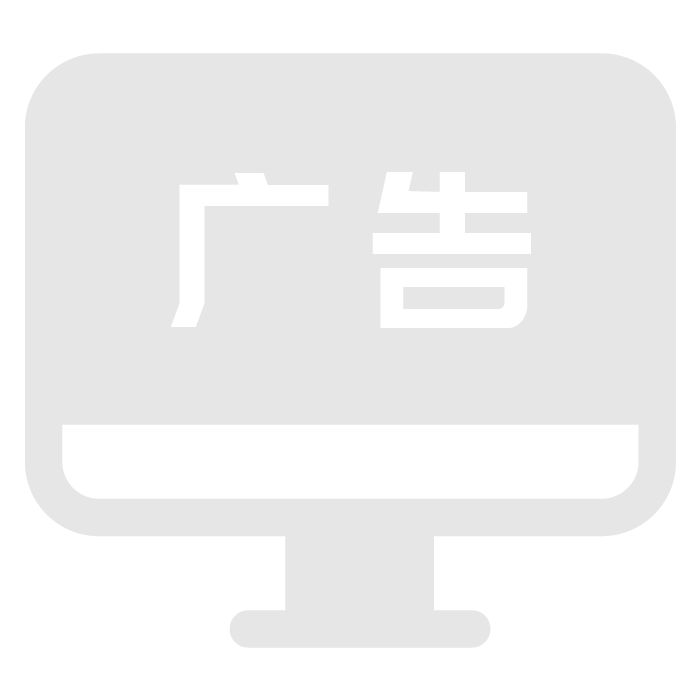 廣告
廣告
 我要
我要
 簽到
簽到

 關注
關注
 客服
客服 TOP
TOP


 粵公網(wǎng)安備 44011202002240號
粵公網(wǎng)安備 44011202002240號